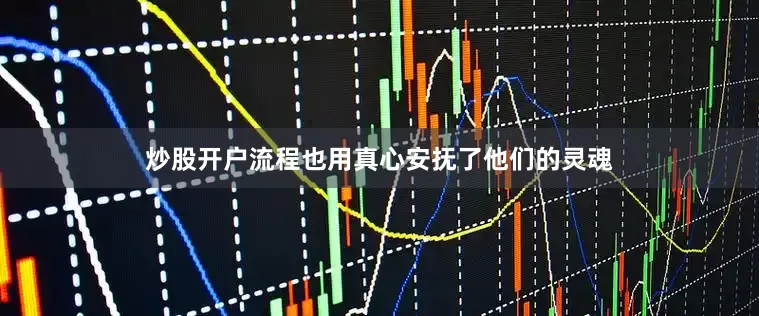一个日本兵的良心债:那天,他三次求情,救下的人是零
后来很多年,东史郎的梦里,总有一股子烧焦的木头混着铁锈味的怪味儿。那味道,把他死死钉在1938年河南汲县的那个凌晨。
天还没亮透,大概三点多钟的光景,整个村子就像被人泼了油,一下子就着了。那火光,红得瘆人,把每个日本兵的脸都映得跟庙里的恶鬼似的。

这不是一场遭遇战,说白了,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戮。一个中队,三十来号人,悄没声地就把村子给围死了。连村口的土狗,都没来得及叫唤几声,就再也没了动静。
进村的流程,简单粗暴得像一套流水线作业。踹门,抓人,找不到人的屋子,直接扔个火把进去,连着土炕和炕上的人,一块儿当柴火烧。

东史郎那会儿,还只是个一等兵,屁大点的官都算不上。他手里攥着一个刚从小孩那儿抢来的铁饭碗,碗上还有点余温。他心里堵得慌。
那天,他破天荒地开了三次口,想替那些中国人求个情。

第一次,是在村里一间堆放族谱的老屋里。士兵们从里面拖出来十二个女人,她们脸上抹着锅底灰,身上套着男人的褂子,可那藏不住的惊恐眼神,一下子就暴露了。
东史郎看着那个最小的,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,忍不住跟中队长嘟囔了一句:“她们,可能不是这个村的,没犯什么错吧。”

中队长,一个叫青田的家伙,斜了他一眼,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傻子,嘴里轻飘飘地吐出几个字:“你管的闲事太多了。”
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可另一幕,让东史郎一辈子都忘不掉。一个老太太,死死地把一个十来岁的孙子护在怀里,藏在墙角。两个士兵上去,硬是把孩子给拽了出来,就在院子里,一刀。

血溅了老太太一头一脸。她嘶哑地喊:“俺娃不是兵!不是兵啊!” 可谁听呢?在当时的华北战场,日军推行的“三光政策”,也就是烧光、杀光、抢光,早就把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野兽。这种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,根本不是什么意外,而是既定方针。
打谷场上,六个壮年汉子被绑着,问他们游击队在哪,粮食藏在哪。几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,翻来覆去就一句话:“俺们就是种地的,真不知道啊。”

青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,命令新兵上。这在日本军队里,叫“试胆”,就是拿活人给新兵练手,捅了第一刀,以后杀人就不手软了。那几个汉子,到死都没吭一声,就那么硬挺挺地倒下去,牙咬得咯嘣响。
村西头的火势最大,风一吹,火舌能窜起几米高,很快就烧成了一片。那十二个女人,被关进了村口的一间木屋,可能是个小祠堂。

中队长挑了两个最年轻的,先进去了。剩下的士兵,就按着军衔,跟领配给一样,排着队在门口等。有人推了东史郎一把,怪声怪气地说:“你不是心疼吗?那你先进去享受啊。”
东史郎没接话,就蹲在地上,死死盯着地上的土。他不是什么英雄,他就是个被战争机器裹挟的普通人,那点良心,在刺刀和枪火面前,脆弱得像一张纸。

临近中午,部队准备撤了。中队长下了最后一道命令:“全部处理掉,不留活口。”
东史郎脑子一热,又冲上去说了第二句话:“如果让他们活下来,他们会感念皇军的恩德的。”
回答他的,是脸上火辣辣的一巴掌。他的枪和刺刀都被收了,被命令去搬抢来的粮食。有人警告他,再多说一句,就按通敌办。
“哒哒哒……” 机关枪的声音响了,像急促的鼓点,敲在每个人的心上,也敲碎了这个村子最后的生机。那些倒下的村民,姿势各异,有的还抱着自己的孩子。
那间关着女人的木屋,也被机枪扫了一遍,然后,一把火。
大火烧到下午才慢慢熄了。东史郎回头望去,整个村子,只剩下黑漆漆的断壁残垣。只有村外那片绿油油的麦田,还在风里摇晃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回到日本后,东史郎把这些经历写进了日记。他想把这些“不该被忘记”的事情公之于众。可这本书的出版,困难重重。
更讽刺的是,他因为在日记里指名道姓地揭露了当年战友的暴行,晚年被那个叫桥本光治的军官以“名誉侵犯”的罪名告上法庭。经过多年的诉讼,2000年,日本最高法院最终判决东史郎败诉。
这个想说出真相的老兵,在自己的国家,输给了那个他想揭露的罪恶。
说到底,战争这台绞肉机,碾碎的不光是敌人的血肉,还有自己人的灵魂。东史郎的故事,不是一个“好人”在坏人堆里的故事,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良知,如何在集体疯狂中被反复撕扯、最终被碾压成粉末的悲剧。他没能救下任何人,连为他们说出真相的权利,最后都差点被剥夺。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无力和悲哀的地方。
富明证券-股票配资穿仓-股票配资平-股票配资免费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